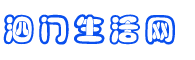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,诸如三跪九叩之类,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,诸如三跪九叩之类,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
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,诸如三跪九叩之类,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还有一些要建立什么“儒教”: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“爱滋”。
中华帝国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[1],斯人已逝。但没有同死、共赴。没有哈姆雷特式的困惑:“还是?这是一个问题。”[2] 但有别样的纠结:“何去何从?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斯人既逝,吾身何寄?在今天的,正如徐志摩的诗句:“我不知道风,是在哪一个方向吹;我是在梦中,在梦的轻波里依洄。”[3]
本来,帝国时代的儒学,那是“妾身分明”的,即所谓“制度的化”和“的制”[5],也就是和帝国制度的婚媾;质言之,那时的帝国就是化的帝国,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举行了婚礼,那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“化”。
不仅如此,那时的,“分明”之“身”是不是“妾身”,抑或竟是“男儿身”,也是一个问题。“制度的化”恐怕意味着:帝国制度是的儿子,而不是的夫君。那位“制度的总设计师”韩非子,不就是的“不肖之子”吗?
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,“制度的化”甚至意味着:那时,的身份到底是不是“妾”?是不是女儿身?皇家与的联姻是不是“纳妾”?甚或尽管是“入赘”,毕竟处于“夫”的地位?抑或双方至少是平等的“同性恋”,犹如希腊雅典当年的“男风”?这些都是问题。
然而近代以来,“化的制度”和“制的”都解体了,帝国已逝,犹存。这时候,孤苦凄切的才陷入了“文君新寡”、“妾身未明”的境地,以至“风尘”,乃至沦为“游魂”[6]。
所谓“妾身未明”,出自杜甫的诗《新婚别》:“暮婚晨告别,无乃太匆忙!妾身未分明,何以拜姑嫜?”根据诗意,在今天看来,该女子算是成婚了,怎么能说她的身份“未分明”呢?原来古代的婚礼,手续比较繁缛,新娘过门三天以后,告夫家之庙、祭夫家之祖坟,如此等等,以“明”其“身”,然后拜见公婆(姑嫜),这才算是正式成婚了。否则,便是“妾身未明”。
当代正是如此尴尬。本来,20世纪的现代新“美人迟暮”之际,是要改嫁“新外王”的;而其选择委身于“新外王”,也就是选择和“与科学”举行“暮婚”。然而很快就闹出了“新婚别”的变故,变成了21世纪的新,心里产生了一种要与与科学“晨告别”的冲动,于是就“妾身未分明”了。
所谓“人尽可夫”,出自《左传桓公十五年》记载的雍姬和她母亲的对话:“(雍姬)谓其母曰:父与夫,孰亲?其母曰:人尽夫也;父,一而已。胡可比也!”[7] 父亲只有一个;丈夫,则天下男人无不可。
当今的,可不就是“人尽可夫”吗?除了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、或被老板“包养”、改“儒”姓为“钱”姓的以外,时而嫁给“左”家(),时而嫁给“右”家();时而随了“马”姓(马克思主义),时而随了“自”姓(主义);时而又姓了“原”(原教旨),时而又姓了“后”(后现代);似乎“名花有主”了,实则“水性杨花”而已。
然而,不论“妾身未明”、待字闺中,还是“人尽可夫”、芳心有主,其实都是“妾妇之道”[8],而非真正的孔孟之道。真正的孔孟之道,那是孟子讲的“大丈夫”[9],原本是“男儿身”,何来“妾身”?
这种“变性手术”,似乎做得很早,早在那位“始”还只是“秦王”之前。比如“伟大的”诗人屈原,最喜欢以“美人”自喻。[10] 这显然是一种上的“变性”、人格上的“自宫”。他(或她)本来很受楚王宠爱,后来被疏远、放逐,于是“远之则怨”[11],自比弃妇,从而自怨自艾、如怨如诉地咏叹着“众女嫉余之娥眉兮,谣诼谓余以善淫”、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[12],乃至寻死觅活,徇情投江。诚“烈女”也!然而非“烈士”也。人们说屈原对楚王的“从一而终”是“爱国主义”,这其实是很可笑的:照此逻辑,孟子离开“祖国”(鲁国)、“移居国外”,到处宣讲儒学,劝人称王,简直就是“主义”了!
自从屈原以来,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“审美传统”,叫做“香草美人之喻”,即:士大夫把自己与皇上的关系比喻为妾妇与夫君的关系。于是,我们读到历史上的许多“怨妇”之诗、“弃妇”之诗,作者所的情绪其实都是对某位“今上”的幽怨和对自己“妾身”的哀怜。悲夫!
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。比如历史上那个真实的,就把自己去京城与勾兑比喻为“买春”,即今天所说的“”。他这首词,全文如下:
天南地北,问何处,可容狂客?借得山东烟水寨,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,绛绡笼雪,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,薄幸如何消得?
想芦叶滩头,蓼花汀畔,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,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,忠肝盖地,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,醉乡一夜头白![13]
这首词的词牌是《念奴娇》,我不知道是不是的有意识的选择。词中所说的“凤城春色”,表面上是说的名妓李师师,实际上是指的宋朝。
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评价其人,而只是说:他声称自己凭梁山的实力来和讨价还价,乃是“借得山东烟水寨,来买凤城春色”,那是何等的男人味!何等的“大丈夫”气概!当然,他谋求“招安”的时候,还是有“卖身”或“求包养”之嫌;[14] 但的“性取向”其实并非只有这一面,还有另一面:“他时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!”[15] 自己要做“丈夫”,那么呢,又不能明媒正娶,而那个时代又没有“婚外恋”之类,就只能是他“买春”的对象了。
词中讲“山东烟水寨”,也颇有意思。其实,山东不仅是水泊梁山“草寇”的根据地,也是的故乡和根据地。在取得“独尊”地位之前,原本是“在野”的,并不“在朝”。我总觉得,比起今天的许多“”来,更像一个真正的。真正的不是“妾身”,而是“丈夫”,是敢的,是要“”的。“汤武”[16],难道不是的传统吗?
不过,买春、是需要谨慎的,弄不好恐怕会染上传统的“梅毒”、或现代的“爱滋”。比如今天有一部分主张恢复“古礼”,诸如三跪九叩之类,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“梅毒”。反之,当年康有为之流以为必须学习现代的“国教”,为此就必须创建“孔教”作为中国的“国教”,甚至不惜委身于张勋所的帝国“老男人”;而今天也有一些竞相仿效,要建立什么“儒教”:在我看来,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“爱滋”。
所以,的身份认同问题,不仅涉及“妾身”是否“分明”的问题,更根本的是究竟是“妾身”还是“男儿身”的问题。
本文开头说到,有学者也提到“妾身未明”。他说:“以现代的价值”、比如“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儒学的价值”,“这样妾身未明的传统文化,如何能令人信服地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之所在?”[17] 对此,我有两点疑惑:
其一,“功利的标准”难道仅仅是“现代的价值”吗?难道中国传统文化中、儒学中竟然没有功利价值?我不禁想起南宋大儒叶适的名言:“不谋利,明道不计功,此语初看极好,细看全疏阔。既无功利,则者乃无用之虚语尔!”[18]
其二,假如“现代中国”的文化认同不能依据“现代的价值”,难道应当依据“古代的价值”吗?那么,“古代的价值”包括哪些内容?是不是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那一套?再者,依据这种“古代价值”而建构起来的所谓中国,那还是“现代中国”吗?作者这种把“传统文化”、“儒学”和“现代的价值”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,实在很成问题!这分明是“棒打鸳鸯”,梁山伯和祝英台谈恋爱,正如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。
在我看来,今天的,在帝国已逝、“妾身未明”之际,首先应该恢复自家的“男儿身”,恢复孟子那样的“大丈夫”本色,再像那样“发扬英雄气概”,大胆地“再买春色”。这里尤须注意:所谓“春色”不是别的,恰恰是“现代价值”。何谓“现代价值”?“核心价值观”讲得很明白:、平等、、都是现代价值的“春色”。唯其有如此这般的“春色”,才值得去“买”。
行文至此,忽然想到:那些话,恐怕有过多的男权主义色彩,女性读者会不高兴。那咱就换一种说法吧:在这个男女平权、同性恋婚姻化的时代里,是否男儿身并不要紧;要紧的是要倾心于“现代价值”这个绝配佳偶,大胆追求,义无反顾,与之谈婚论嫁,以求百年好合。
[1] 李鸿章:光绪元年《因事变筹画海防折》。转引自梁启超:《李鸿章传》,中华书局2012年版,第六章。
[3] 徐志摩: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》,原载1928年3月10日《新月》月刊第一卷第1号。
[10] 关于屈原诗中的美人自喻,例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注“哀高丘之无女”:“女以喻臣。”《楚辞章句离骚序》说:“宓妃佚女,以譬贤臣。”《文选》吕向注“无女”:“女,神女,喻也。”钱杲之说:“女喻贤臣可配君者。”刘梦鹏说:“女,,比贤者。臣之事君,犹女之事夫。正士入朝见忌,犹之入宫见妒。”王泗原《楚辞校释》注“高丘无女”:“女,,以喻贤者。”转自杨成孚:《〈离骚〉“求女”解新论》,《南开学报》(哲社版)1995年第5期。
[14] 关于是否主动寻求招安,其实是有争议的。据《宋史张叔夜传》记载:“贼闻之,皆无斗志。伏兵乘之,擒其副贼,江乃降。”可见其不得已。《宋史》: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